我被提升为亲生命,但现在我是亲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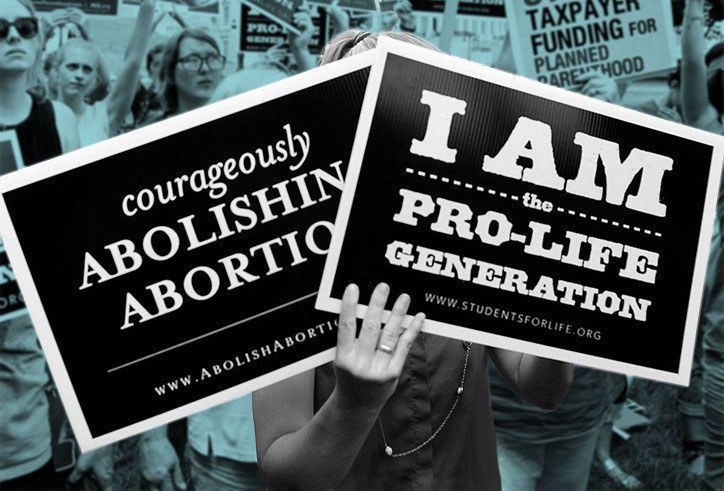
Gabby Weiss长大后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活动家。这位22岁的新墨西哥人被养大,认为堕胎是邪恶的,并在她的家人和地方及全国的亲生活事件中得到证明。但今天,Weiss的工作与她所预期的完全不同:她是NARAL Pro-Choice America的实地项目组织者,NARAL Pro-Choice America是该国最着名的支持选择组之一。是什么导致某人留下他们被提出来相信的一切 – 并致力于为她一直被教导的事情而奋斗是一种可怕的罪? Weiss与Glamour分享了她的故事.
我的家庭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们是Quiverfull运动的一部分(有些人说Duggars来自 19孩子和计数 是成员,虽然他们否认它)。它被称为Quiverfull运动,因为有一节经文 – 诗篇127:3-5-将孩子与箭袋中的箭相比较,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箭袋。成员非常政治,他们的哲学是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孩子,因为他们是文化战争中的箭头武器.
整个事情都基于非常直接的性别角色。我了解到这些男人是家庭的主人,女人几乎只是为了生孩子而存在。我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老的一个,按照许多人的标准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小家庭。而且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也会长大成为一个妈妈并且有很多孩子 – 我总是被告知这是我的目的和命运.
我也被提升为非常政治化的。我的父母带我们去圣达菲州首府和D.C.的国家首都游说他们的大问题?流产。我们甚至都在华盛顿的三月生活中一起游行。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堕胎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相信强奸或乱伦的例外情况或母亲的健康状况 – 我从不质疑我们的观点有多么尖锐。堕胎是错误的,同性婚姻是错误的。我的全家都是在家接受教育,所以除了父母告诉我的事情外,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文化.
当我18岁的时候,我去了弗吉尼亚州Purcellville的Patrick Henry学院。这是一所专为在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运动中长大的孩子而设的大学,旨在让保守的基督徒在政府或法律或非营利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
我是幸运儿之一,因为我要上大学;我们运动中的很多女孩甚至都没有机会。我记得问过我的父母,比如,“如果我要结婚并开始生孩子,这值得吗?”但是有人告诉我,在我结婚之前有几年的事业是可以接受的家人;他们说也许我可以成为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因为我是金发碧眼的,或者我可以成为下一个Lila Rose [一个着名的反堕胎活动家].
但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在高中时,我开始意识到禁止同性恋婚姻只是走得太远了。如果同性恋者结婚,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进步的过程仍在继续,但我的堕胎信念是最后的事情。真正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被强奸了。这不是特别暴力的事情。但我意识到,出于某种原因,他只是觉得有权在不事先咨询我的情况下做出有关我身体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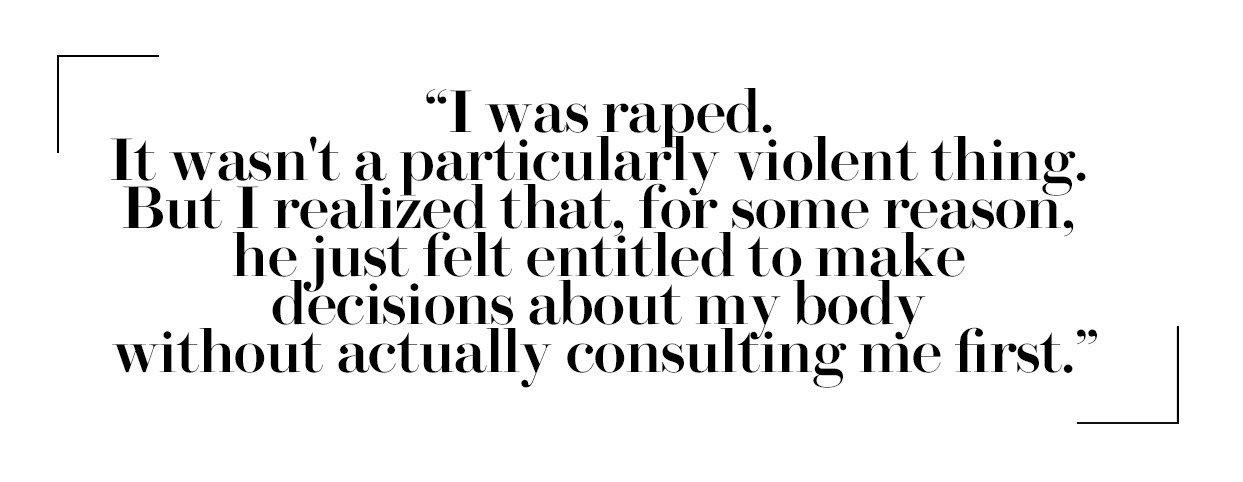
在那之后,我感到内心需要再次要求控制我的身体。我立刻得到了纹身。所有这些政治事物只是点击到位 – 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那个世界,无论是童贞承诺还是严格谦虚的着装规范,或者这种假设我将要长大并拥有一百万婴儿 – 他们感觉就像是暴力袭击在我的控制权 我的 身体.
我很清楚这一点 一世 我想成为一个决定我身体的人,无论是与谁发生性关系,还是我成为了母亲。任何人都会觉得他们有权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真的很暴力.
我的父母让我成为政治人物,为事情制造噪音。因此,对于我可以看到周围发生的所有这种不公正感到安静,我感觉不对。我想让校园和世界变得更美好。有一次,我甚至公开谈论被强奸,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大学如何应对性侵犯。我很清楚,在那种环境中很多人并不真的相信强奸甚至是一件事。他们认为这恰好引用了一句话 – 不引用“荡妇”,或者因为你处于这种状况。这是意识形态的另一部分,女性的身体不是女性控制的东西。我们只是一种消费品.
我留在帕特里克亨利大学的其余部分。这很粗糙,我不会说谎。我被批评为进步活动家。我的父母也很紧张。在我大四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回到家,试图与我的妈妈和解,因为我妈妈在学校里直言不讳的活动家似乎很难过。.
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我告诉她,“看,我不会在政治上与你达成一致。我不会成为你文化大战中的箭头。你能不能像女儿一样爱我虽然我在政治上不同意你的看法?“在回答之前,她问我两个问题。她问我是否认为同性婚姻应该是非法的。 “不,”我告诉她。她问我是否认为Roe v.Wade应该被推翻。 “不,”我再说一遍。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接下来说的话:“好吧,不,我不能爱你。”
这就像是我心中的箭。但是站出来做什么 一世 相信?我为这个选择感到自豪。我不会回到那个女性被视为财产并且只是生殖器官的世界,即使这意味着失去了我妈妈的爱。我不能回去。我必须找到另一条前进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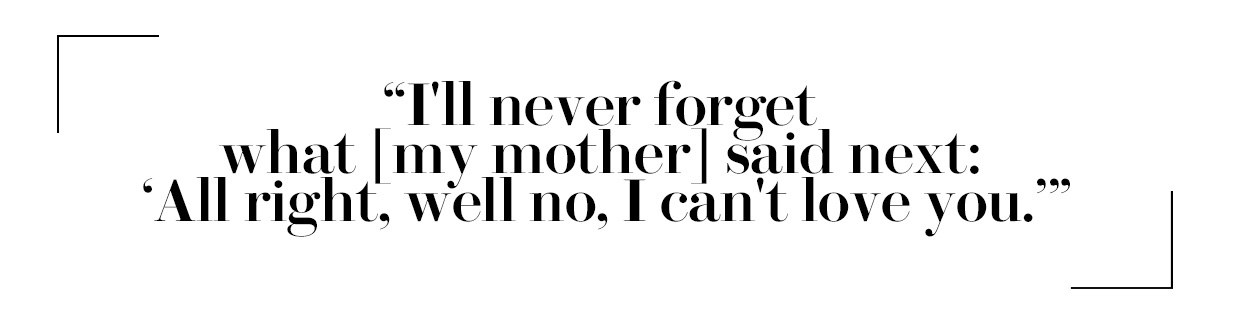
我想找一份工作,让我可以被那些肯定女性代理和自治的人所包围。我非常喜欢组织和倡导。并且知道这种保守的管道是如何建立和资金充足的,以及创建保守派领导者的效率如何,我觉得我需要努力反对这一事业.
我在高年级的第二学期和NARAL实习。保守和反堕胎成长,我已经知道NARAL是谁。它们是人们总是谈论的重大坏事之一。我想积极致力于创造一个女人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价值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现实的世界。毕业后,我全职回到了NARAL.
有很多人喜欢我 – 年轻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现在有了疑问,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一个理解的人。有时我会跟那些说“嘿,我总是被告知堕胎是错误的人说话。但是女权主义者说它不是。你怎么看待这个?”我喜欢这些谈话。因为我知道完全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因此,让某人了解您正在经历的事情真的很有帮助。我经常谈论他们希望世界在一天结束时的样子。当人们走开时,他们可能不会说,“哦,是的,我现在是亲选择的。”但他们经常说,“我想要的世界是一个女性受到重视并具有代理和自主权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决策者。”
对于那些相信我曾经相信的人,我感到同情和沮丧。我知道他们长大了这种说法。我知道它的真实感。当我在那里时,我真的相信我只关心婴儿。我从未注意到女性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因为女性甚至不被认为是完整的人类。当我看到像特德克鲁兹和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时,这也令人沮丧 – 这些人认为他们有权告诉女性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我知道那些长大的男人。这是关于权力的。无论是性生活还是生育或日常家庭生活,一切都围绕着拥有权力的人。他们希望通过社会或政治手段来维持这一点.
我失去了我的家人;我失去了我的大学朋友 – 他们都以为我会下地狱。我仍然在建立我的新社区并找到我的员工 – 但是我能够每天走进工作,我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受到尊重是巨大的.
如果我能在四五年前与年轻的自己交谈,我会告诉她好奇。我的旧世界很多都是在说外面世界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并且会下地狱。这就是谎言。我会告诉我的十几岁的自己不要害怕。尝试新的想法。自己评价一下。推迟。寻找真相.
这个故事是我们继续报道的一部分 美国的堕胎:引爆点. 在最高法院关于堕胎准入的可能历史性决定的风口浪尖上,我们将调查最新的堕胎立法如何影响妇女和医生;回答你最常见的问题;并且看看这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中双方活动家的下一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