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堕胎国家的亲选择活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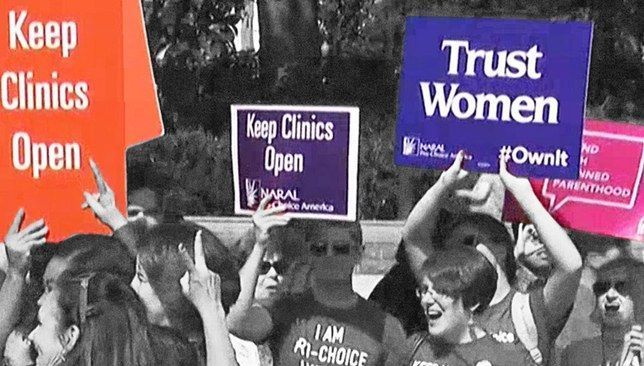
2012年,一名反堕胎抗议者在头上打了一个显示巨大胎儿的标志的Alison Dreith.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托德·阿金最近在电视上提出他的理论,即“合法强奸”从未导致怀孕,这意味着没有人需要在堕胎禁令中包含任何例外。该州的紧张局势正在高涨,而Dreith在Planned Parenthood的工作意味着她处于第一线。抗议者每天向她施加骚扰,但这是第一次对她进行身体殴打。 Dreith的对手确实用他们的论点击中了她的头部.
今天,Dreith是NARAL在密苏里州的附属公司的执行董事。要在那里进行堕胎,女性必须接受国家指导的咨询(这是为了阻止她进行手术)。咨询必须亲自提供,并在72小时的等待期开始之前进行,这意味着女性必须分别进行两次旅行。对诊所本身的限制也非常高。诊所必须满足门诊手术中心的要求,这要求房间,门,窗和走廊的大小,并要求医生让医院承认特权.
密苏里远非孤身一人。自2010年以来,数百个TRAP(堕胎提供者目标法规)法律已经通过州立法机构,政治家们在2015年在46个州引入了数百多项法律 – 396项法律.
“我恨其他州认为他们是一种特殊的雪花,因为我们都在一起,”Dreith说。 “在有大多数地区的红州,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战斗带到地方一级。这将是漫长的道路,但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有很多女人喜欢Dreith。他们生活在TRAP法律使堕胎几乎不存在的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阿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路易斯安那州,印第安纳州,德克萨斯州。这些活动家跨越年龄,种族和民族,社会经济背景和宗教信仰。他们的工作范围从国家级政策倡导到基层努力,如挨家挨户拉票,堕胎基金筹款,临床护送 – 甚至形成女权主义朋克摇滚乐队.
作为支持生活状态的亲选择活动家,他们面临着不可能的困难。他们当选的官员,社区和他们的家人不同意他们的工作。他们是超人和超人。他们的激进主义可以使他们面临身心上的风险.
尽管有反对力量,但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所在州的人们对公民权利的侵蚀感到愤怒,并且被地方政府所挫败,这些地方政府因伪装成保护措施而浪费税收。堕胎权利运动可能正在达到临界点,但这项工作还远未完成.
尖叫成虚空
Harmony Glenn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名为Indy Feminists的女权主义活动家的创始人。她白天为一家生殖保健提供者工作,每周花30-40个小时争取获得堕胎。 Indy女权主义者散布请愿书,参加抗议活动,并在新闻播报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报” – 就像Purvi Patel在她试图自我诱导流产后被捕一样.
“我认为红州的活动分子是顶级的耐力运动员,”格伦说,“这不是一场短暂的比赛。这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比赛。什么都没有快速或轻松。“
格伦说,这不仅是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听到的挑战,也是全国其他国家的挑战 – 包括其他州的支持选择活动家和组织.
“在这些问题上,大型国家集团并没有进行大量投资,”格伦说。 “我认为他们认为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命运,觉得他们的钱会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但是右翼团体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对于右翼,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维持,但是对于左翼,必须花费太多的努力来移动针一点点。我觉得我们正在尖叫成一个虚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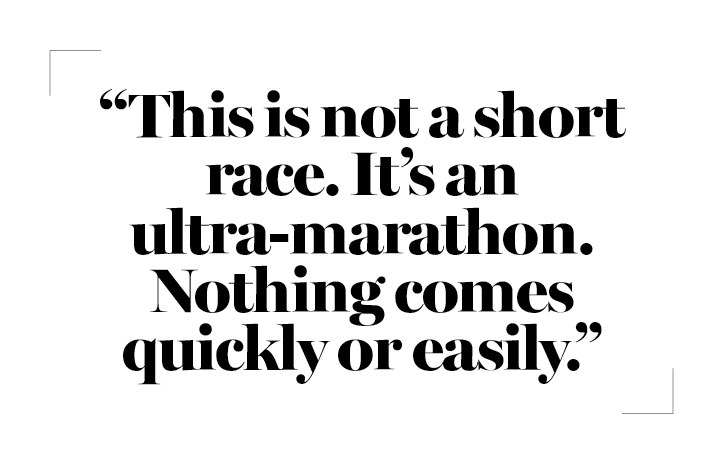
像格伦一样,Kierra Johnson也对红州在堕胎谈话中被撇去的方式感到沮丧。约翰逊来自格鲁吉亚,是Urge的执行董事,该组织让年轻人参与有关生殖和性别公正的活动,特别是在中西部和南部各州.
“不幸的是,对南方人有很多负面的误解:我们需要得救,我们不知何故倒退,我们是一个失败的原因,”约翰逊说。 “现实情况是,南方有着强大组织的悠久历史。我们需要做这项工作的人,尽管他们来自哪里,但正是因为他们来自哪里。“
宗教在空中
约翰逊表示,在保守派方面“大声喧哗”可能会让整个州看起来像是一种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然而,让更多的人参与运动需要满足他们所在的地方并尊重他们的文化背景.
“在红色地区,我们不能反对宗教和灵性 – 它在空中,”她说。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南方浸信会或者认定为天主教徒而将人们割掉。”
我采访过的许多活动家强调了参与宗教团体的重要性,并表示他们的信仰是他们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Abby Agnew首先参与了Urge作为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学生。她来自堪萨斯州南部的一个小乡村小镇,每个人都“很有生气。”阿格纽认为既是宗教选择又是亲选择,她说她说话的每个人都混淆了.
阿格纽说:“有很多人既有宗教信仰又有亲选择权,我不认为这是你必须要挣扎的事情。” “我曾经听过一位女士说,尽管有宗教信仰,但我们不是支持选择,而是因为它。那跟我在一起。“
虽然阿格纽认为支持选择和宗教并不相互排斥,但她表示,这可能会导致她的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她称之为反堕胎。当她在家时避免冲突,她很少把她的工作带上去.
“当我告诉他们我的实习是什么时,他们就像是,’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认为这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反映出来?’“阿格纽说。 “很难听到你所爱的人所关心你的意见。我希望他们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开放
导航如何,何时以及与谁进行某些对话是许多堕胎活动家持续关注的问题,他们常常在说出来的愿望和维持和平的愿望之间感到矛盾。但是说出来是支持选择运动的基石,特别是在需要大规模文化转变的保守国家。减少堕胎的耻辱感与在首都露营和游说立法机构一样重要.
Zoraima Pelaez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学生,她公开分享了她的堕胎故事。 Pelaez将成为她移民家庭中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人。她的姐妹都是青少年母亲; Pelaez说,他们面临的斗争和障碍告诉她决定进行堕胎。她从未考虑过广泛分享她的故事,但她意识到公开讲话是她影响变革的最有力方式之一.
“另一方想要的是让你感到孤独,排斥和害怕,”佩拉兹说。 “分享我的故事 – 说出’我这样做了,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我是我今天的女人因为它’ – 这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即使他们不同意我或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它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堕胎是完全正常的。“
不断的威胁
Sarah Banning在抵达阿拉巴马大学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一个校园女权主义组织,开始在塔斯卡卢萨的西阿拉巴马州妇女中心护送,她说在那里进行身体和口头骚扰并不少见.
“护送可能会受到威胁,因为前往诊所抗议的人是最忠诚的,最疯狂的疯子,”班宁说.
在达拉斯一家诊所护送的活动家Sara Nickells说,不同的抗议团体有不同的策略。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不具有侵略性,但许多人采取难以承受的恐吓和恐吓手段。反堕胎抗议者经常单挑护送,拍摄走进诊所的人的照片,并写下车牌驶入停车场的车牌数量.

“天主教徒出来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因为他们除了站在那里祈祷之外什么都不做,”尼克尔斯说。 “但是有一个人会说’你是那个应该被流产的人’,他因为在诊所的窗户里尖叫而被捕。还有一个人曾说过百事可乐是由流产婴儿制成的,所以下周,我们喝了樱桃百事可乐。“
这些类型的互动可能在情绪上令人筋疲力尽,更不用说可怕了,但尼克尔和班宁都说这种灾难是值得的.
“我希望保护这些正在进入诊所接受治疗的女性,”班宁说。 “他们应该感到安全和舒适。通常患者需要等待3-4个小时,他们会出来和我们交谈并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我听他们需要说的话,鼓励我。“
即将到来的斗争
今年早些时候,最高法院裁定关键堕胎案件 – 全女人的健康诉Hellerstedt这对德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的TRAP法律造成了打击。这对红州的活动家来说是一次胜利,他们终于感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许多人表示,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是生殖权利斗争的转折点,不仅从司法和立法的角度来看,还因为它可以帮助激发更广泛的参与运动。.
德克萨斯州利利斯基金公司执行董事阿曼达·威廉姆斯说:“现在我们看到了动力和力量。” “但德克萨斯州在公民参与的每个可能名单中都处于最底层:女性注册人数较少,青年注册人数较少。人们越来越关注并开始醒来,我真的相信,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投票,事情会有所不同。“
在立法机构和一般人群分享你的观点的地方生活可能更容易,你不觉得你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攻击,而是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做激进主义工作 – 尤其是当那个地方是你的家 – 有自己的奖励.
“我认为这就是让德克萨斯成为一个活跃分子的特殊地方 – 这项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佩拉兹说。 “我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在其他地方做这项工作,但这是我们最需要它的地方。”

